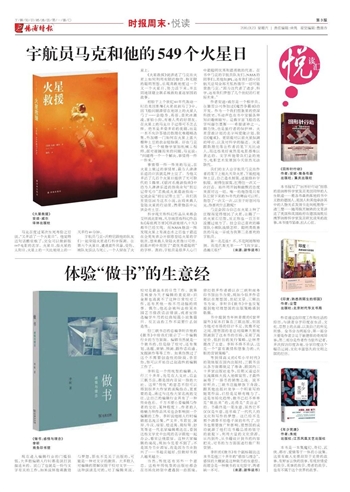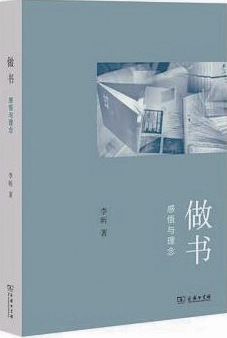但三联书店的总编李昕在他的《做书》中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编辑行业的方方面面。编辑当然就是一个做书的,但是除了校对,还有策划、选题、营销、预测、跟作者沟通、发掘新作等等工作。如果你熬过了这个不需要创造性的阶段,恭喜你,你可以开始自己创造性的编辑工作了。
李昕是一个传统型的编辑,入行三十多年,先是在人文社,后去三联书店,都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大社。这里“传统”的意思不但可以得到很多大作家的熏陶指点,更重要的是,通过与这些大家名流的交往,让自己的编辑行业具有了一种传奇色彩。千万不要小看编辑与作者的交往,某种程度上,作者的人格魅力和作品风采也会影响到一个编辑的工作。李昕说他刚入行时编辑部名流云集,严文井、韦君宜、屠岸、牛汉、绿原、楼适夷、聂绀弩、舒芜等老一代名家编辑都还在,看到这些文学史中出现的名字跟他一起办公,着实让他震惊。这种大家编辑的境况,现如今是看不到了,不是因为书业凋零,而是因为书业勃兴了——书越卖越好,但做好书的人越来越少。
当然,传统还有另外一个意思。这些年传统型的出版社都会在市场化转型中遭遇到一些困境,曾经很多作者都以在三联和商务印书馆出书为荣,现如今很多作者都以在理想国、世纪文景、三辉出书为荣。李昕在《做书》中也反复提到他对理想国的出版策略感到敬佩。
书中提到当年林青霞的《窗里窗外》原本打算在三联出版,但因为他对市场的估计不足,犹豫不定之间,理想国的老总刘瑞琳大胆地预测到了这本书的市场,采用了高定价、低折扣的发行策略,让林青霞改了主意。李昕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富有激情和想象力的、大胆的营销策略”。
等到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的简体版在国内出版时,三联书店从各方面都做足了准备,跟国内三十多家出版社竞争,后期又通过在主流媒体大投入地做宣传,才最终赢得了一场书的销售之战。说不好听点,三联书店能够放下身段,跟其他出版社竞争一个明星写的随笔作品,已经是足够有魄力了。这是市场化趋势,做书已经不单单是“做出来”的,还得是“卖出去”的。书最终是一笔生意,虽然它不仅仅是生意,还承载了一代代人的文化和写作的梦想。这已经不是那个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年代了,好书也需要推广和影响,理想国的成功就源于他们在书籍品质的坚守的前提下,利用大量的文化资源,从内到外,从书籍设计到书的内容把关,对书的方方面面进行推广和营销。
李昕的《做书》有个副标题说这本书是他三十多年的“感悟与理念”,感悟的大概就是这种做书的生意经,而理念是一种做书的文化坚守,两者缺一不可。(来源:新华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