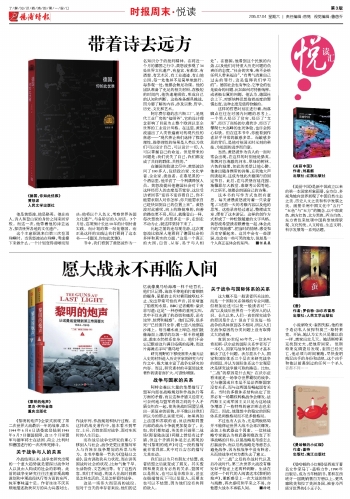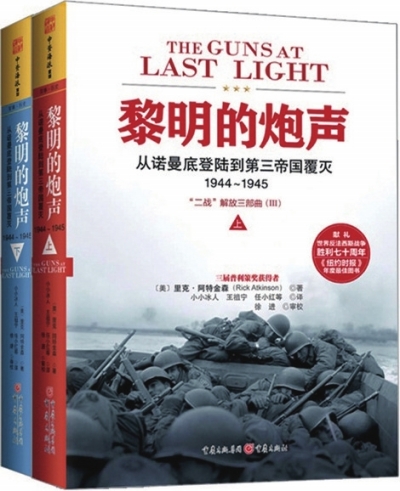关于战争与人的关系
冷战结束以来,战争史研究出现的一个重大趋势就是要探讨战争对人以及由人构成的社会的影响。此前的战争史研究往往注重宏观战略谋划和中观战役执行等方面的东西,纯军事味道十足。作者往往不厌其烦地描述敌我双方的兵力兵器对比,作战序列、作战规划和执行过程。在这样的战史著作中,基本看不到军官、士兵、百姓在面对战争、面对生死时的人生百态。
而冷战后战争史研究的重心下移到人与社会,战争史更注重描写军人与百姓在战争期间的所思与所为。本书序幕第一节名为《登陆日之前》,没有讲敌我兵力状况,而在讲英国战时社会的状况,比如气象干旱、生活物资、文艺演出等。有了这些内容,我们才知道,英国人在战时到底是怎样生活的,又是怎样看待战争。
这是一场伟大而崇高的战役。但对于当天的幸存者来说,他们的记忆就像奥马哈海滩一样千疮百孔。他们只记得,海浪不停地拍打着钢铁的舰身,晕船的士兵对着雨披呕吐不止,发出异常可怕的声音,甚至堵塞了船底的水泵。BBC记者戴维·豪沃思写道:这是“一种恐怖的垂死尖叫,其中不仅充满了的恐惧和痛苦,还有诧异、惊愕和疑惑”。他们记得,很多死尸已经面目全非,横七竖八地倒在沙滩上。每当潮水涌上岸边,他们就像海面上漂浮的垃圾一样不停地翻滚,救生衣仍然系在身上。他们不会忘记眼前这片满目疮痍的海滩,而这片海滩名字叫“奥马哈”。
研究视野的下移使原来大量无法入史的材料进入历史学家的研究与写作之中,极大地丰富了战争史研究的内容。而且,研究素材的丰富使战史著作的读者面扩大,可读性增强。
战争与国家的关系
阿特金森以大量的笔墨描写了盟军内部在战略规划和作战执行等方面的矛盾,而且这种矛盾又经常无可奈何地与盟军将领之间的个人矛盾交织在一起,使英美战时同盟呈现出一派复杂的面貌,并不像以往我们所以为的那么亲密无间。如果再加上法国和苏联的话,反法西斯同盟内部的政治斗争就更加复杂了。比如,我们都知道,英美在开辟第二战场(即登陆法国)问题上曾经有过矛盾,但这个矛盾具体是怎么展现的呢?《黎明的炮声》对这一段的描写就非常具体,其中对丘吉尔的描写尤其生动。
我们总以为只有朋友才结盟,或者结盟之后就变成了朋友。其实盟国和朋友没有必然的关系,盟国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非敌非友,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可以是敌人,而朋友也可以不结盟,因为他们没有共同的敌人。
关于战争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这大概不是一般读者所关注的,而是一个国际关系领域的专业问题,但稍加论述可以使一般读者对“二战”以及战后世界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在探究战争的原因是什么?但由于引发每一场战争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所以人们在战争原因的分类问题上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
直到20世纪50年代,一位名叫肯尼斯·沃尔兹的国际关系学者写了一本《人、国家与战争》的著作才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沃尔兹从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层次来研究战争的原因,并认为国际体系这个宏观层次是研究战争最可取的路径。比如,“二战”的原因是什么呢?在沃尔兹看来就是一场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它与德国或日本是不是法西斯国家没有关系,而与这两国是崛起国有关系。当时的多极体系结构决定了世界必有一场霸权转换战争会爆发,法西斯主义或军国主义只是为这场战争增添了一些特殊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已。因此,他理想中的稳定的国际体系是两极格局而不是多极格局。
不过也有人认为,光是两极格局并不能保证世界大战不会再次爆发,还加上核武器这个因素。一位核战略专家就认为核武器彻底改变了军事战略的目标,以前战略是考虑怎么打赢战争,而以后的战略是考虑怎么避免战争,因为核战争中没有胜者,从而使战争对双方都失去了意义。
在“二战”之后的冷战时代以及后冷战时代,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爆发似乎验证上述两种判断。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人阅读这本《黎明的炮声》,重新感受上一次大战的惨烈与残酷,再次感叹和平来之不易,亦惟愿大战永不再临人间。 ■徐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