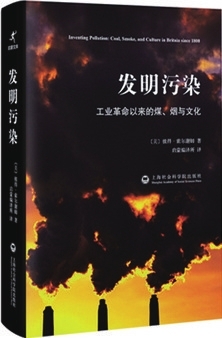该书在探讨环境问题时,并没有泛泛而谈,而是穿越时空的隧道,在大量文献和数据的基础上,以英国十九世纪主要城市空气治理侧重点,从政治、经济、科技、医学、人文的维度,进行综述性的分析。全书共分为十一章,阐述了煤炭与空气、污染与治理、健康与文明之间的内在较量。
作者在第一章《煤炭、烟和历史》中摆出这样的事实:“当今世界,有三十亿人生活在城市中,相当于世界人口的一半,他们中有很多人忍受着不适于呼吸的空气。”我们生活中很多人抱怨空气质量如何糟糕,其实只要生活在大城市,不管你愿不愿意,都要面对空气受到污染的现实。
越是工业生产起步早的地方,空气污染的时间也就更早。工业革命中,蒸汽机当然是功臣,而作者却认为:真正引爆工业革命的,是煤炭的大规模开采与使用。煤炭开启了现代文明的新时代,同时也将地球引入环境污染的时代。
英国煤炭资源异常丰富,20世纪初期,一直都是欧洲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年产量2.29亿吨。如果仅仅是因为大量的煤炭生产,或者是蒸汽机的普遍使用,都不足以使英国成为19世纪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但是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改变了一切。工业革命时期,随着工厂用蒸汽机取代畜力和水力,各行各业对煤炭的需求迅猛上升,并且持续增加。
煤炭在燃烧中,不仅释放了可利用的能量,还释放了大量的烟、烟尘、酸性水汽。尤其是煤烟中,会产生毒灰、二氧化硫、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然而工业革命期间,英国人竟然认为煤烟是无害的。当时,煤烟弥漫在英国的很多城市,对此民众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污染并不是来自煤炭等自然资源的使用,而是产生于自然生活的过程。他们把疾病的传播归咎于瘴气,而瘴气是一种不可见的气体,被认为是腐烂的动植物散发出的。如此一来,哪里发现的腐烂生物最多,就认为哪里的环境污染最严重,沼泽、丛林、墓地、污水坑、下水道是污染之源。
19世纪末期,英国的公共卫生专家、城市改革者、记者重新定义了煤烟,不再认为它是城市环境可接受的一部分,而是把煤烟视为一个城市问题。本书中写道:“人类具有了超越以前难以超越的环境限制能力,但又没有能力预判或控制他们的新技术产生的后果。”对环境恶化的担忧,当时一些激进的艺术家和作家表现尤为明显。一些人开始怀念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乡村,期望英国彻底放弃工业之路,回归淳朴的乡土社会形态中。
按照常理,既然全社会都充分认识到烟雾的危害性,那么接下来要看如何治理了,而空气治理并非想象的一帆风顺。在民众的要求下,1912年当“一战”打得正酣之时,英国气象局成立了大气污染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目的是对英国各大城市的烟尘沉淀进行科学测量,并对空气质量进行抽样分析。然而,这种类似学术研究的组织,大企业主和资本家并不放在眼里。为了获取源源不断的财富,他们不期望减少煤烟的排放,更不愿意看到企业关门停产。他们把制造煤烟的罪魁祸首推给城市居民,理由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煤炭而排放的煤烟比工厂的更严重。英国政府部门在这个问题看法上两面摆动:一面要顺应民意,必须减少煤烟的排放,另一方面又不能和资本家们翻脸,因为他们是政府部门的缴税大户,得罪不起。
当空气污染已经影响到所有人的健康和生存质量时,英国社会的各利益阶层都不得不做出相应的妥协。1956年,英国颁布了《清洁空气法案》,这项法规在空气污染整治方面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英国相继出台一系列更加严格的生态环保法规。在空气污染、生态环境治理方面,英国人不仅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其他欧洲发达国家也同样如此。2015年12月18日,英国关停了最后的煤矿企业——约克郡凯灵利煤矿,这也标志着英国彻底结束了煤炭时代。从鼓励煤炭生产,到控制煤炭使用,再到现在的告别煤炭,英国走过了一百多年的路程。
在整治生态环境过程中,必须面对经济发展不能停滞、民众生活质量不能下降的现实。这些年来,为了应对这一难题,英国和欧美各国专注于高新技术和金融经济的发展,那些能耗高、污染重的企业,陆续迁移到发展中国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发展中国家为了经济快速增长,是以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有关碳排放控制与减少问题,如今成为国际外交领域的焦点,发达国家总是指责发展中国家破坏了地球生态环境,然而这些发达国家,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的工业革命中,就已经成为生态环境恶化的始作俑者。如何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寻找平衡点,考验着各国政府的社会治理水平与智慧。
本书所讲的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及其之后对待煤烟的认识变化、空气污染治理的刚性策略,为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带来诸多思想上的启迪。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的关键机遇期,不能因为发展经济和提高生活水准而破坏日益脆弱的生态环境,当然也不能为了生态环境的修复而停止经济建设。从政府政策的角度看,执行现有的环保法律法规不能松懈,厂矿企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要在新能源新材料技术创新中有所作为。对于每一个公民而言,生态环境既然关乎所有人的生命健康和生存质量,那么真正地践行绿色理念,则是应有之举。
(来源:新华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