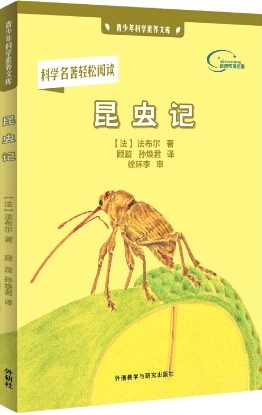《昆虫记》
法布尔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当网络和各种移动阅读设备日益成为人们难以割舍的心头之物,当越来越多的90后沉迷于网络构筑的虚拟世界,当越来越多的有闲人士醉心于WiFi和微信带来的快捷而廉价的人际沟通媒介时,我们不得不承认,网络已经成为人们身边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很多人不由自主地把大把的时间花在面对无生命的电子宠物上。然而,人类毕竟是自然之子,是千百万年进化的产物,人不能脱离自然界而存在,自然界有太多奇妙的事物等待我们去探索、去认识,历史上无数次人类想要主宰自然的企图都使得人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心中缺少对自然的爱与敬意,他很难感受到生命的尊严。
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应该把一部分闲暇时光用在到野外看看这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上。几年前《博物》杂志只有几万册的月发行量,现在逆市上涨至20余万册。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欣喜地看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最新推出的彩图精译版《昆虫记》。没错,市场上已有无数《昆虫记》版本,这恰恰说明中国读者对《昆虫记》的厚爱。然而,绝大多数版本或者将法布尔尊为伟大的文学家,或者尊为杰出的昆虫学家,或者认为是二者的完美结合。
其实,《昆虫记》只不过是法布尔随性写下的观察笔记,各篇之间并无巧妙设计的关联,法布尔在文学上的最高荣誉也只是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另一方面,在目前从事昆虫学研究的专业人士眼里,法布尔也算不上昆虫学家,他的研究以个人兴趣爱好为主旨,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研究,而且观察对象大多是常见于法国乡村的昆虫,试问,有谁在有关科学史的著作中找到过法布尔的名字?然而,法布尔的光芒不会因为他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而褪色,实际上《昆虫记》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文精神,远远超越了其中介绍的昆虫知识。“何当南戒栽花暇,细校虫鱼过一生。”法布尔正是这样一个人,他一生清贫,却以观虫为乐。在昆虫的伊甸园里徜徉,无论生活多么艰辛他都能坦然面对:他从不抱怨自己因为出身贫寒未能在少时接受良好的教育,也不抱怨自己因为经济能力欠佳而与大学教授职称擦肩而过,更不在乎远离城市的繁华重返幼时熟悉的乡村。野外的自然博物馆给法布尔带来了一个无痛的世界,他宁愿在乡下陪伴一只只可爱的小虫子,也不愿在城市里与某些庸俗的上流人士为伍。如果你不知道这些,是无法品味《昆虫记》的真实价值的。其实,法布尔真正的过人之处是他细致入微、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以及对生命和自然的热爱与尊重,他以人性观虫、以虫性鉴人,形成虫人交相辉映、人虫彼此相融的唯美境界。这正是这一版《昆虫记》与其他版本不同的地方——突出法布尔作为博物学家的贡献,着力展现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昆虫世界。书中有大量精心绘制的彩色插图:争巢的石蜂、趴在树根上的若蝉、摆出武斗姿势的螳螂、啃食丈夫尸体的雌螳螂、惨遭金步甲毒手的松毛虫……无不生动逼真,让人如临其境。
这本书由日本九州大学博士、中国农业大学昆虫学系副教授徐环李审稿,弥补了译者在昆虫学常识方面的欠缺,如不完全变态昆虫的幼虫应被称为“若虫”等。徐教授认为,《昆虫记》是“博物学家、文学家”法布尔所著的“系列科学随笔”,他对书中与当代昆虫学认知不符的内容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毕竟作者已经去世100年了。今人阅读《昆虫记》是为了感受小小昆虫“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恪尽职守”的精神。
复兴博物学的倡导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曾经说过:“知识、情感和价值观中,知识不是最重要的,情感要比知识重要。”《昆虫记》正是这样一部带领人们进入优雅情感境界的作品,让人们油然产生不枉度生命的感觉。前一段时间,一位18岁的史学天才“英勇”地作别人世,如果他肯花时间到大自然中走走,看一看为了给自己或后代创造更多生存、繁衍的机会,屎壳郎的意志力是多么坚强,也许就不会如此轻生了吧。要知道昆虫的祖先四亿年前就已经生存于地球之上了,一只小小飞虫的身躯里藏着四亿年不断进化得来的基因库。如果他知道这一点,会不会对生生不息的自然界充满敬意,会不会对所有生命倍加珍惜呢? (来源:新华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