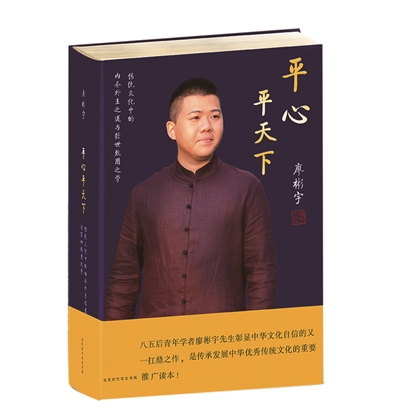在读中学期间,他曾给他的校长写过数万字的信,这位校长从中读出了他的“宏伟志向、坚定信念与深厚文化”,更有“出乎意料、自愧弗如、枉为人师”之叹,所以校长还曾叫全班同学拿出笔记本记下“廖彬宇将来一定会成栋梁之才,十年、二十年后请大家见证”的话。
离开学校后,他继续苦心孤诣钻研国学经典,20出头就登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北大讲学,26岁出版200余万字的煌煌大著《国学旨归》,28岁创办大型书院——四观书院、四知书屋等高端讲学机构,31岁出版《平心平天下》。
他是凭着悟性,直接通过古人著作体察圣心圣学的。这样的人,学习重心往往不在言,而是心;不是术,而是道。关注言与术者,一般可以训练为研究者,关注心与道者,则可能成长为圣心圣学的承载与光大者。承载者非训练造就,乃禀赋所致也。研究者固可宝贵,然终属枝叶;承载者尤其难得,盖因其怀化大本大源也。
故廖彬宇这一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路,须由自身先天的卓然禀赋与后天的因缘造化共同促成,不是谁都可以模仿的,但一旦走通,往往可成正果。子曰:“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吾夏文脉,非赖研究者赓续之,须靠道统承载者发扬光大之。
廖彬宇这种独特为学的途径,使他不会被时尚扭曲,而可大道直行,体悟天心,得其真传。
当下谈论传统文化,颇有一点热闹。摇旗呐喊者何其多也,或名噪江湖、或爵重庙堂者亦为数不少。仅图名爵者、指向利益者、受托代言者、变政易道者……总之五花八门,各有所图。有人力图把百余年来中国反抗殖民、谋求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与吾夏五千年文明史割裂开来,把百余年救亡图存艰苦奋斗所形成的历史功勋、思想成就,与吾夏先民的大道圣学对立起来。此种趋势发展下去,不但百年浴血奋战受到质疑,今日之国体、政统都将受到威胁。所谓传统文化,竟成武器。既悖天道,亦违“化成天下”之训。此系当今国学热中一大隐患,颇有僭夺主流之势。
廖彬宇一直独立求学,未陷任何门派,未受邪学荡涤,故心清路正,一意务道。他心中的传统文化,不是武器,而是春风。在奋战百年起死回生之后,吾夏正在大本大源上全面恢复生机,春风与生气同在同来也。
廖彬宇学问宏富,更深得儒学“经世致用”神髓,颇有安民济世、匡扶社稷之志。他曾以《国学旨归——经世致用之学与内圣外王之道》为题给学生授课,其著作则有以《平心平天下》为题者,讲题书题均揭示其治学宗旨。不少对传统文化缺乏了解的国民,担心“传统文化热”意在复古,廖彬宇的研究作为一个个案,有助于化解这些国民的忧虑。
廖彬宇既是一个无学历、无背景、无资历的“三无”之人,更是一个智商高、情商高、灵商高的“三商皆高”之奇才。他是一位有社会责任、社会理想,时刻关心民族前途和人民命运,替社会和人类思考的真正的文化者。
复兴千年古学,目的肯定在于造福当世。所要坚守者,乃古学之道,其道用于后世,必将经过创造性发展,找到适当途径与方法。赵武灵王在动员朝官支持“胡服骑射”时指出:“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三王随时制法,因事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也不必一道,而便国不必古。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史记·赵世家》)不守古道,自伤其魂,不变旧术,自囚其身。自囚其身则难于经世致用。
文化是为人民的利益、尊严、幸福服务的,是为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兴盛服务的,也是为建构政治认同和社会凝聚力服务的。明乎此,才有经世致用之基础。《平心平天下》于此多有阐述,值得读者思量。
除此之外,廖彬宇还有一个特点,或因其怀通经致用之学,故于社会现实中总能“左右逢源”,一呼百应。而此种禀赋实能帮助有志者在现实环境中,创造宣学申志之条件。须知为学者甚多,能播布其学进而学以致用者甚寡。盖因禀赋各异,难求其全也。
近代以来一百余年,从清末直至本世纪初年,民族文化经历了由盛到衰的百年挣扎,出现了一大批迷茫、自虐、崇洋媚外的负能量风云人物,准确表现了挣扎的焦虑、绝望与乖谬。民族文化的复兴,不可一蹴而就,那是一场激荡百年的政治文化运动,必将经历死里逃生、挣扎奋发的炼狱考验,必将造就一大批有信念、有激情、有才学、有担当的正能量风云人物,他们将准确体现复兴途程中的自信、坚毅、豪迈,和返本归元、脱胎换骨的大仁大勇,而呼风唤雨的风流人物,将是他们的代表性人物。为中国崛起、文化复兴而战,就是这个时代的经世致用。(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