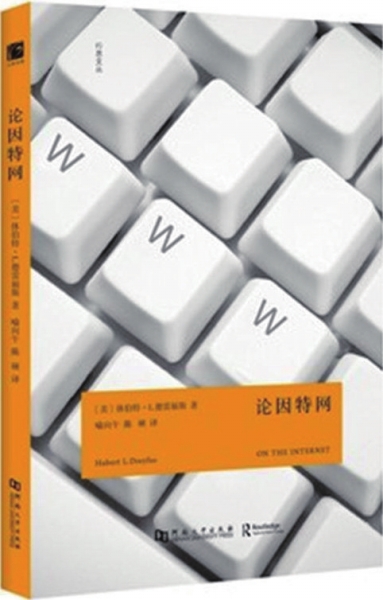休伯特·L.德雷福斯
河南大学出版
作为出生在上世纪20年代末的哲学家,休伯特·L.德雷福斯可谓见证了信息论从无到有的历程,而他也从未停止对于由“比特”塑造的人工智能、互联网的研究和批判。早在1972年,德雷福斯就在《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极限》一书中批判了人工智能研究的局限性。
如果说德雷福斯的《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极限》是人工智能“警世通言”,那么德雷福斯的另一本书《论因特网》则是一本关于互联网发展的“醒世恒言”,德雷福斯展现了他对互联网社会深层次影响的清醒判断。
革新信息组织方式
早期互联网的先行者们都在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把线下的信息数字化,早期以新闻为主。比如世界上第一个门户网站雅虎,以及中国的新浪、搜狐、网易等等。这些网站通过技术、人力将报纸、杂志的新闻变成数字化的内容,完成了互联网的第一步。
当所有信息都以“平等”姿态示人时,其最直观的冲击就是信息爆炸带来的焦虑和无助,德雷福斯在1999年完成本书第一稿时对于解决这个难题颇为悲观,他甚至认为“由于网络内容的爆炸性增长速度,开发出成功的搜索引擎很快将变得不再可能。”但来自斯坦福大学的两个年轻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给德雷福斯带来诸多灵感。
佩奇和布林的想法听起来很简单:用网页的超链接价值衡量这个网页的价值,进而自动化完成网页的排序,将有价值的网页优先呈现给用户。在互联网内容(超链接)快速增长的背景下,网页重要性完全可以通过超链接的多少与质量来“投票”。
德雷福斯在1999年刚刚成立不久的Google身上看到了解决信息爆炸的最好办法。事实也的确如此,Google自一成立就秉承“整合全球信息,使人人皆可访问并从中受益”的使命,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每天全球数亿人通过一个搜索框了解世界,获取知识。
社会依然没被解放
几乎每一代新技术的出现,都会被人移植到教育领域。
如今新技术如虚拟现实、新理念如社交知识互动、新一代互联网受众,似乎重新定义教育的所有要素,比如真正实现远程教育。但德雷福斯并不这样看,他认为“当教授特定的技能时,老师必须是具象的,并鼓励情感代入。”更进一步来说,技术无法改变教育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对事物和人的真实性的感觉,以及与之交互的技能,都取决于我身体无声的幕后工作。”另一方面,因特网对于社会复杂性的影响力也微乎其微。德雷福斯花费了很大篇幅探讨信息高速公路上的“虚无主义”——这是一种对于不同东西判断的价值观,认为一切都是同等的,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值得为其献身。
德雷福斯援引克尔凯郭尔1846年一篇质疑公众和媒体导致虚无主义的文章展开论述,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大众媒介的普及带来了特有的公共领域讨论,报纸具备可匿名性的特点也加剧了公众讨论热情,但“公共领域存在于政治权利之外,意味着人们可以对任何事情持有自己的观点,却无需有所行动。”
比如,国内近几年来兴起的自媒体群体,由于绝大多数并不具备持续生产高质量观点的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自媒体人开始生产“新闻”——他们并非像专业记者前往事件第一线调查、采访从而获取一手资料,而是用搜索引擎、社交媒体现有的内容去整理,并用一些耸人听闻的标题进行营销推广,影响恶劣。
很多人把上述现象归结于互联网的影响,但本质上而言,这不过是人性或者社会万象的一种折射,也只是一个维度的折射。
那么未来呢?德雷福斯的乐观建立在他对人性的颂歌里。“只要我们仍然还是血肉之躯的人,那么网络可以发挥作用……这并非无视自身的局限与脆弱,而是因为没有我们的身体——如尼采所言——我们将什么都不是。” (来源:新华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