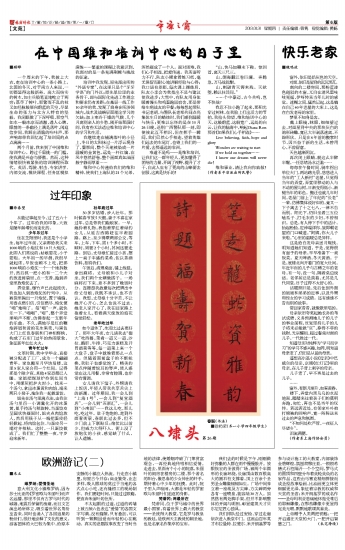窗外,依旧是铅灰色的天空。对面,依旧是屋脊的沉沉黑瓦。南向的二楼房间,那粉蓝漆色斑驳的木窗,兀自在清风里吱吱晃摇,伊呀传来当年儿时的感觉。迷糊之间,猛然记起,这是躺在自己40年老屋的大床上,这是在白发老母的家里。
梦里不知身是客。
戴上眼镜,眯眼,细细望过去,对面屋脊中央的那块灰白的鸽形砖雕,竟已大半剥落迷离,不辩形状。只是在6年前的搬家时节,因兴奋于新的生活,未曾用心,不曾留意。
天色越渐阴沉。
再次闭上眼睛,就这么半醉半醒,一任思绪汤水泛滥……
每每在午餐时间,骑车拐出单位大门,两站路光景,悠悠进入当年的“工人新村”老屋,只觉得当年的弄堂,弄堂里移动的人与不动的屋与树,日渐变得低小,渐褪当年的彩色。搬迁也就几年时间,老屋门前上了年纪的“长老”一辈,仿佛集体说好似的,竟又一下子离去了十之七八,一律不告而别。阳光下,仍旧坐着三五位嗑瓜子、打毛衣的少妇,不曾相识。总是,有人停下手中的活计,抬起粉脸,定神端详你,旋即朝老屋的门口喊道。“阿姨,你大儿子来啦。”心里的温暖总是异样。
这是给白发母亲送月规钱,明知道她们知道,于是,觉得很有面子的母亲,早早准备下一桌饭菜。夏天啤酒,冬天黄酒。于是,底楼北向开着门的宽大灶间,年近半百的儿子与古稀之年的老母,有一句,没一句,隔着桌边说话。老邻居总是羡慕,尤其是几代同堂,日子过得不太舒心的。
话题照旧是,先后住到外面的姐姐和弟弟的近事,以及外甥和侄女的学习成绩。还有谁谁不告而别的故事。
常回家看看,就像歌里唱的。母亲依旧夸奖起她长孙的考试成绩,义务预测她儿子的儿子的事业前程,反复坚持儿子的儿子将来必能做“官”,挣得不菲的钱财,光宗耀祖,超过餐桌对面的儿子,一代胜过一代。
知道母亲对纯粹为“学习而学习”的学习不感兴趣,如同,明知道母亲老了,仍旧是从前的母亲。
遥想高尔基小说《母亲》中巴威尔的母亲,京剧《红灯记》里的母亲,在儿子背上刺字的母亲。
儿子老了,早不再是过去的儿子。
……
窗外,有新月渐升,如雾黄昏。楼下,弄堂内黑乌乌的水泥地面,踏踏来往着孩子们的莫明奔跑,匆忙,再也不是当年的玩伴。若远若近处,有邻家卟卟拍打棉被的回响声,竟一阵阵送来过去的声息和氛围。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泪流满腮。
(作者系上海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