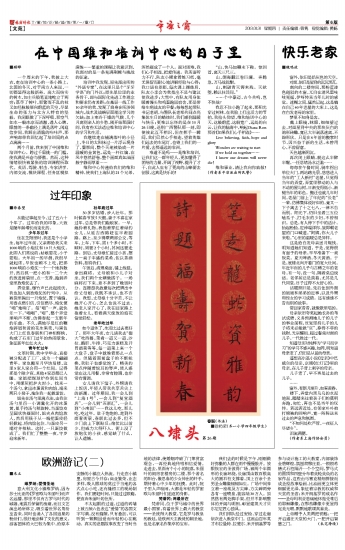从能记事起至今,过了五六十个年了。过年给我的印象,大致是随年龄增长而变化的。
少年乐过年
住在芝阳里时,我还是个小学生,每年过年前,父亲都给我买来1000响的小炮仗和10只大炮仗。此即人们常说的:姑娘要花,小子要炮。大年初一的早晨,我很早就起床,早饭也顾不上吃,把那1000响的小炮仗一个一个地拆散开,然后抓一把小的和一二个大的放进裤袋里,点一支香,跑到弄堂里放炮仗去了。
弄堂里,爆竹声已此起彼伏,我也加入到放炮仗的行列中。从裤袋里掏出一只炮仗,置于墙缝,用香点燃引信,引信燃尽,炮仗便“啪”地响了。每“啪”一声,就快乐一下。“啪啪”、“嘭”,整个弄堂里响声不断,仿佛奏起一支新年的乐曲。不久,满地尽是红的鞭炮碎屑和黄的花生果壳,与黑色大门上红色春联和门神相辉映,构成了石库门过年的热闹景象,象征新年红红火火。
青年忙过年
文革时期,我中学毕业,直接被分配进了工厂,成为一个翩翩青年。家也搬至月华坊后楼,这里5家人家合用一个灶间。记得那是个除夕夜,其他4家恐都已入睡。家姐把煤球炉拎到灶间当中,用煤灰把炉火封小。找来一个汤勺,拿出冰蛋黄和肉馅,端来两只小凳子,拖住我一起做蛋饺。
姐先在汤勺里滴点油,由我往汤勺里舀一小调羹化开的冰蛋黄,姐手持汤勺稍旋转,当蛋饺皮呈圆状快凝固时,姐夹点肉馅放入,然后用筷子从一端把蛋皮轻轻掀起、将肉馅包住、与蛋皮另一端对齐相粘。这时,一只蛋饺做成了。我们忙了整整一夜,守岁迎来新年。
壮年跑过年
30多岁结婚,步入壮年。那时候春节放5天假,妻子不喜在家过年,总是带我们跑娘家。一早,她拎着礼物,我抱着穿红着绿的女儿,从延吉西路赶往半淞园路。路上,至少得乘两部公交,等车,上车,下车,需1个多小时,不顺时,则要2个小时,其间还要走路。到后,丈母娘忙接过小孩,摆上一桌子丰盛的菜肴,佐以茶酒饮料,招待我们。
午饭后,清理桌面,铺上线毯,拿出麻将。丈母娘和小儿子对坐,我们两个女婿做搭子。一场麻将打下来,差不多到了晚饭时分。连襟怨我故意每次把牌出中给丈母娘,我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我想,丈母娘十分辛苦,不让她开心开心,怎么也说不过去。她老人家开心了,我在回家路上抱着女儿,看着满天绽放的焰花倍觉轻松。
老年吃过年
如今退休了,生活比过去更好了。那年大年夜,女儿请我去“德大”吃西餐,菜肴一道又一道,沙拉、鹅肝、牛排、巧克力蛋糕及开胃酒菜等等,每一道菜上来一个大盘子,盘子中就堆着那么一点点。但随着面前盘子的不断轮换,我肚子也感觉饱了。精美的菜点伴随着悦耳的琴声,使人感觉在这儿用餐,非常有腔调,也非常有情调。
女儿请我下馆子,外甥请我上饭店,年轻人带我共享舌尖上的新潮。过年期间,我一会儿到“上海1号”,一会儿到“复宣酒店”,一会儿到“苏浙汇”,一会儿到“小南国”……我这儿吃,那儿吃,吃过年。肚子饱饱的,走到外面看街景,春联比过去多,但不少门前上下联贴反;炮仗比以前少,但威力大得吓人。街上没了放炮仗的小孩,感觉缺了什么,让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