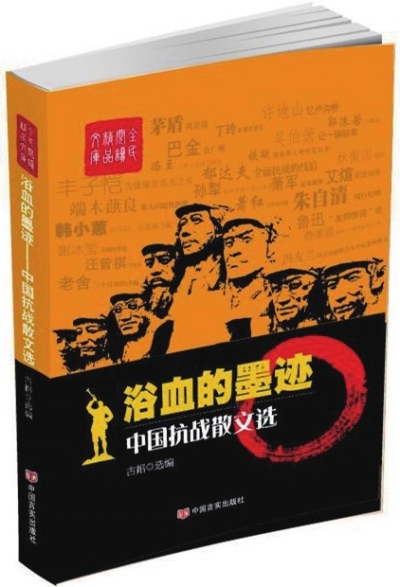古耜(选编)
中国言实出版社
抗战散文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写出了不同作家眼中和心中的抗日战争,透过带有作家经历、性格、情感乃至体温的笔触,传递出打上了“我”的印记的抗战话语。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曾经的集体记忆和共同经历,这场战争所具有的有目共睹的历史情境和基本进程,以及中国作家面对这场战争所表现出的彼此相通的立场、感情、态度、取向,决定了百态千姿的抗战散文,最终又必然会形成某些共同的色彩和相近的质地:
第一,抗战散文高扬国家意识,统摄抗战全局,实录多方战事,具有实事求是的信史品格。身为战地记者的臧克家,写出《津浦北线血战记》,描述了台儿庄一战中国军队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与此同时,郁达夫也来到徐州前线,出其笔端的《在警报声里》,透过英雄师长池峰城的讲述,不仅凸显了47位敢死队员以生命换取胜利的壮举。当时任教于齐鲁大学的老舍亦投身战地采访与写作,一篇《三个月来的济南》,直言齐鲁战事,既批评了战争到来之际,政府的准备不足和军事的调度不当,又称赞了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中国士兵的忠勇坚韧。曹白是深受鲁迅关注和爱护的青年木刻家。抗战爆发后,他参加新四军的救亡宣传工作,陆续发表了《潜行草》《富曼河的黄昏》《到张家浜去》等一系列作品,以雕刀般的笔墨,让一大批“在受难里面战斗”(胡风语)的游击健儿,活现于历史的天幕。孙犁的《采蒲台的苇》写白洋淀老百姓用鲜血和生命掩护八路军战士。应当看到,这些作品尽管传递了不同的战地信息,反映了异样的抗战画面,但分明充注了同一种国家意识和民族情怀。正是这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保证了当年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
第二,抗战散文关注历史现场,直面战争节点,还原人物和细节,呈现出较高的认知意义和文献属性。对于亲历抗战的作家来说,抗战散文是他们的经见撷取或记忆捡拾,很自然地承载了战争的风云变幻与慷慨悲歌。所有这些经过时光淘洗和岁月打磨,最终化作年代写真与历史镜像,成为后人重新触摸和认识战争的重要通道。朱自清的《绥行纪略》和《北平沦陷的那一天》,前者通过作家赴前线慰问的见闻,勾勒出绥远抗战多方动员,众志成城的生动场景;后者从作家身临其境的感受出发,记录了历史上那个挥之不去的痛心日子。萧军的长篇散文《侧面》,讲述了作家在抗战初期由临汾到延安的一段经历,把当时晋陕一线紧张而混乱、灼热而悲凉的抗战局面,传达得既真切又充实;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歌声》等作品,落笔抗战中的延安,而又专写这里热火朝天的物质生产和激扬勃发的精神生活。
第三,抗战散文关注战争中人的命运与价值,赞颂正义的反抗,呼唤和平的回归,揭露战争造成的民众灾难和人性扭曲,表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和以战反战精神。一切战争都是人的战争,一切战争散文所表现的都是战争中的人。具体来说又有两个相反相成的维度,即一方面无情揭露战争和侵略者的滔天罪恶;一方面热情讴歌反战争和反侵略的斗争精神。在前一维度上,一批抗战作家从切身体验出发,零距离书写了战火下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苦难境况:丰子恺惊闻家居被毁,禁不住发出《还我缘缘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的悲愤之音;苏雪林身处尴尬艰窘的避难生涯,只能以《炼狱》这样的牢骚和自嘲来排解;缪崇群的《流民》写难民的颠沛流离,食不果腹;方令孺的《忆江南》写江南老家的惨遭洗劫,文物损毁,无不血泪满纸。显然,这些作品对战争的残酷性、破坏性和反人性,发出了最严厉的声讨和谴责。在后一维度上,浴血沙场,保家卫国,构成了抗战散文久久回荡的主旋律。围绕这一旋律,一系列可歌可泣的人物形象纷至沓来:张自忠将军骁勇善战,为国捐躯,他生前的生活却是罕见的沉毅自律,廉洁简朴(梁实秋《记张自忠将军》),还有杨靖宇、赵一曼、投江的“八女”、跳崖的“五壮士”、在芦荡中坚持抗战的新四军伤病员……他们以血肉之躯构筑起国家的长城,同时也写就了一个民族的心史。
第四,抗战散文在艺术上亦有积极的经营与探索,留下了若干足以流传的篇章和应当借鉴的经验。抗战散文同样涌现了一些艺术上精彩亦精致的篇章,如茅盾的《风景谈》、孙犁的《山地回忆》、梁实秋的《跃马中条山》、端木蕻良的《有人问起我的家》、王鼎钧的《红头绳儿》、汪曾祺的《跑警报》等,都是流光溢彩,质文俱佳的好文章。(来源:新华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