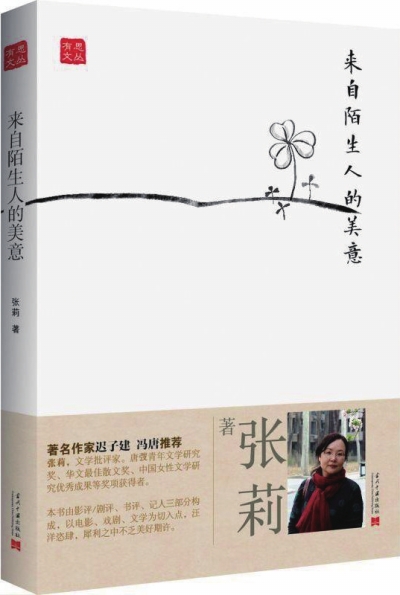但或许是“批评”二字给了读者先入为主的味道,让人觉得批评家只是喜欢充当作品缺陷的批判者,好像他们从来不会发现作品之美。事实上,这并不准确。评论文章最大的一点要求就是“不虚美隐恶”。而张莉认为这应是写作的自由,张莉在书中写道:“作为批评家,我希望自己写下的文字能做到听从内心的声音;我也希望自己能做到秉笔直书,坦陈己见。这些目标并不容易达到,它实在需要我们终生与身体中那个怯懦和懒惰的‘我’进行不屈不挠地搏斗。”因此在面对阎连科这样的作家时,她也显得十分坦诚。
张莉的评论消解了我们与作品之间的隔阂,批评家之“悦”嵌入到她的评论文本中。她的触角伸到那些隐秘的角落,思索作品中的幽微之光,乃至于读者甚至能透过文本思考人生。当大家兴致勃勃地讨论春晚小品涉嫌性别歧视时,她却提出社会对女性话语的双重矛盾。又或是关注青年作家的写作成长之路,尽管她认为她写的还不是足够好的,她依然对他们报以诚恳的褒奖和热切的希望。
张莉的批评有着温柔的力量。当她在读王安忆的对话录时表示“适度的沉默是美德”,她认为“《对话启蒙时代》仿佛是音乐声里的呛声,其功能是‘去魅’——它把小说本身的含混性、间接性全部消解,把所有与文学艺术有关的光泽全部抹掉,只留下可怕的观念和思想。它让人觉得只有理解小说的某一个路径才是正确的。”这正是张莉一直主张的好的批评所应具有的文体意识。
要维持这种评论方式就需要批评家的心足够“柔软”,柔软即同情。同情是理性的根源,做评论也是如此。从小的教育似乎让我们形成了对待事物要一分为二,但比辩证更重要的是“同情”。一个具有“同情心”的批评家,往往会看到比文本更广域的世界。这里的同情不是指对作者或文本人物、文艺作品单纯地做出道德判断,而是应包括借由同情所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如性别意识、存在、反思。当然,这一切的指涉都来源于文本或者艺术作品。可是大多数批评家的“同情”都被遮蔽了,写出来的文章只能是干涩的、肤浅的、没有见识的,这样的批评文章是没有“烟火气”的,自然无法获取读者之“悦”。
在关于电影《黄金时代》的影评《萧军朋友圈对萧红的“残忍补刀”》中,张莉先是对电影忽略萧红的精神求索、文学追求发出诘问,后对萧军形象的处理表示质疑,这样一部被萧军朋友们叙述回忆的电影自然就在一开始有了倾向性,注定电影表现出来的萧红只能是一位小家子气、偏执、敏感、任性的民国女青年,而忽略了“这是一个对大时代和卑微个体一视同仁的作家,这样的选择和追求,是应该受到尊敬和重视的。但在电影中,萧红的写作在当时影响如何、年轻人如何读她、同行如何评价她、她如何无视批评执著写作,全是空白。当别人不能理解她的很多所作所为时,她也是被动的、失语的”。
在《雕塑工作室里的疯女人》里,她评价卡缪尔的疯癫、痛苦、歇斯底里以至于最后的失语,都可以理解为“一个弱势女子对男权社会的激烈反抗”。
这种反思意识不仅反映在张莉对作品的评论,也反映在她对自身的质疑。在阅读《亲爱的提奥》时,她在书中自省:“我是一个凡俗之人,曾对北京街头面容不堪的外地人,对那些在工地上端着大饭盆呼噜噜吃饭的民工侧目过。几个月来我不断地在读这本书,在与心中的凡·高对话时,我时时觉得羞愧不已。贫穷是罪恶吗?贫穷应当受到歧视吗?为什么一个受过人人生而平等教育的青年,说的与做的总是背道而驰。”
如今张莉的“同情”已根植在她的各种文章中,一定程度上和她的研究领域女性文学有关。(来源:新华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