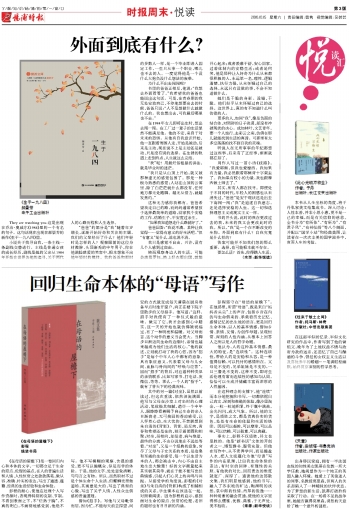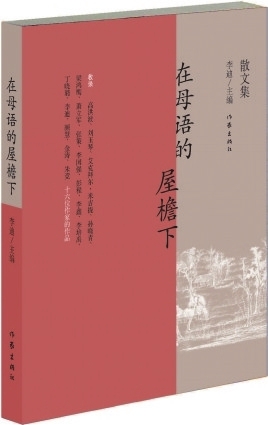彭程
线装书局
《在母语的屋檐下》是一卷回归内心和本体的文字,一切都立足于生命的原点,伦理的基点,在人的普遍生活和人情、人性恒常之处款款落笔,做从容、准确、朴实的表达,写出了通透、蕴藉、经典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
彭程的耐心,使他在处理个人写作资源时,表现得特别的克制、节制,不看到表面之下,不“烂熟于胸”,不真的明白,不痛彻地感受到,他绝不写。他不写模糊的观察、含混的感受,更不写以偏概全、似是而非的体验。于是,他的文字,处处意象清晰,句句言之有物。所以,虽然取材不过是个体生命个人生活,但螺蛳壳里做道场,其寓意是大的,写出了典型的心像,写出了关乎人情、人性众生俱感的普遍道理。
譬如《招手》。写他与父母毗邻而居,因为忙,不能每天前去探望,问安的方式就变成每天清晨在厨房准备早点时推开窗户,向正在楼下院子里散步的父母招手。他写道:“这样,招手对我便有了一种仪式般的意味。做完了它,我才会感到心中踏实,这一天的开始也就仿佛被祝福过,有了一种明亮和温暖。对父母而言,这个动作的意义当会更大。当脚步日渐迈向生命的边缘时,亲情也越来越成为他们生活的核心。”他的叙述,立刻就打动了我的心弦,因为“招手”是每个中年人心中都有的意象,具有象征意义,代表着父母与儿女间、血脉与骨肉间的“呼唤与应答”。因而“招手”的背后,对应着种种类似的亲情联系,比如写家书、打电话、发微信,等等。那么,一个人的“招手”,就有了普天下的经典况味。
其中的另一篇《对坐》,虽然以前读过,但这次重读,依然泪流满面。他写与父母在沙发上对坐时的心理活动,笔致极其细腻,道尽一个中年人,眼睁睁看着赐予自己生命的亲人日渐衰老、无可挽回的苍凉感受,让人怦然心动,生大忧伤,不禁联想到朱自清的《背影》。背影,虽反向,青春和希望还是在的,预示着团圆和相聚;对坐,虽相向,却是老、病与绝望,最终的分离,不由分说地在不远处等着。“对坐”,又是一个经典的意象,穷尽了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本质,是沧桑和至痛的生命感受,每一个以生活为本的人,都会被击中,内心不由自主地生出大酸楚!好的文字衡量起来其实极其简单,就在于能不能写出经典情感,引起人们心灵上的共鸣与共振。从接受学的角度说,彭程的《对坐》与朱自清的《背影》构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学生课本应该选在一起,对照着阅读。因为彭程的启示,感到面对生命的原点、恒常的伦理,老旧的题材也有日日新的内涵。
彭程坚守在“母语的屋檐下”。在他那里,所谓“母语”,既是来自“妈妈舌头尖”上的声音,包括乡音在内的与生命俱来的、承载着历史记忆、感情记忆的出生地的语言,更是回归生命本体,以人的基本情感,譬如乡情、亲情、友情,为创作母题,呈现恒常、深刻的人性内涵,从根本上回答人之所以是人的哲学命题。
他认为,人的这种基本情感,最大的特征,是“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带给人的是安稳和从容,是一种值得信赖、可以托付的感情所在。父母是不变的,兄弟姐妹是不变的,一日三餐是不变的,这种不变,即对生活伦理有常而连续性的感知与认同,恰恰可以生成并储藏丰富而深厚的人性基因。
在这种理念的支撑下,他“连续”而本分地挖掘和书写,一切都依据自己真实、深刻和准确的体验,像沙里淘金,一粒一粒地积累,终于囊中满盈,金光闪闪,成大气象。所以,他的文字,是质胜之文,都是货真价实的货色,处处有生命的体温和生活的烙印。因而可以凝眸,可以摩挲,可以品味,可以信赖、可以敬重,可以典藏。
事实上,彭程不仅质胜,其文也是胜的。他是“新书话”文体的开创者之一,博览群书、腹笥充盈。但他在写作中,从不卖弄学问,而是撮盐入水,把人文底蕴化为他“母语”写作的内在肌理,让自我生命体验的表达,有时空的回眸、有理性的关照、有他我的对比,因而表达的维度就宽广、深厚了。通读他的这部散文集,我们明显地感到,他的书写,融入了苏东坡的旷达,陶渊明的淡然,袁中郎的性情,肖邦的俊逸……种种质素的融会贯通,使他的文字显得那么儒雅、优雅、典雅,于无声处,美不胜收。 (来源:新华悦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