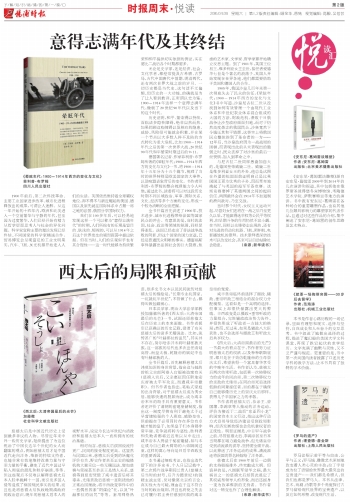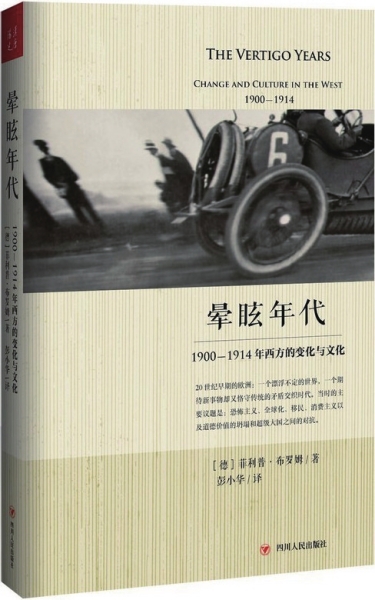我们在100多年后,可以轻易地发现这样一个可以称为“意得志满年代”的时期,人们所抱有的乐观是盲目的、肤浅的、短视的,可以从1914年之后这个世界发生的剧烈震荡中提出依据。但在当时,人们的乐观似乎也有其合理性——这一时代能够为持续繁荣和和平提供切实依据的例证,实在要比二战后各个时期都要多。
无论是史学家,还是经济、社会、文化学者,都经常提及古希腊、古罗马,古代中国唐代中前期、明清两代,还有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岁月。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不无偏颇,但历史的一大功能,的确就是为了让人看到教训,正所谓以史为鉴。1900-1914年这样一个意得志满年代,像极了20世纪90年代以及当下的这个时代。
历史证明,和平、繁荣得以持续,面临诸多隐性障碍,绝非自然而然。如果罔顾这些障碍以及相应的隐患、威胁,风险很可能就会积蓄,并在某一个节点以大多数人猝不及防的方式转化为重大危机,比如1900-1914年代之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90年代和平繁荣时期过后的9·11。
德国著名记者、作家菲利普·布罗姆所著的《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一书,将1900-1914年十五年分为十五个篇节,梳理了当时的世界特别是欧美国家的大事件,以及喧嚣表象背后的变化。书作者菲利普·布罗姆的整合梳理能力令人叫绝,通过此书,读者将可以对这段历史时期不同区域政治、军事、国际关系、文化、经济等多个方面的变化,形成一个较为清晰的全面把握。
全书开篇首先讲述了1900年,技术进步、城市化进程带给法国等国家民众的冲击。有意思的是,当时的法国,社会、政治等领域的氛围,同样显得紊乱。法国已经走出了普法战争战败的阴影,但这个国家的国力衰退,已经是普通民众明晰的事实。德雷福斯事件暴露出法国社会的巨大裂痕,焦虑的艺术家、文学家、哲学家都开始确立反思主题。到了1901年,英国王位易主,维多利亚女王去世,接任者爱德华七世是个著名的浪荡子,英国人开始发现在世界各地,他们都需要借助于美国和德国人的合作。
1905年,俄国沙皇几百年来第一次彻底失去了民众的信任。《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书中写道,沙皇尼古拉二世从没找到如何有效管理一个由现代工业体系和中世纪农业体系混合组成的大国的方法,财政危机、溃败于日俄战争让沙皇政府颜面扫地,而对于仍然高度愚忠的俄国民众,沙皇竟然下令镇压其和平情愿,这事实上将俄国民众整体推到了革命者的一方——12年后,当沙皇政府因为一战战局的困顿,而表现出此前从未表现出的脆弱之时,民众丢掉了对沙皇的最后一丝畏惧,加入到革命之中。
与尼古拉二世同样愚蠢加自大的,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威廉二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他总是试图在外婆的祖国面前证明自己是比英国国王更为优秀的子孙,因而草率地挑起了与英国的海军军备竞赛。这场竞赛磨掉了英德两国之间的起码信任,两国最终会在1914年不加遏制的滑向敌对,乃至交战。
当时那个时代,女权主义运动兴起,尽管妇女们还将在一战之后乃至更久以后,才能赢得选举权等公民平等权利,但早期斗争的作用仍然不容小觑。在当时,同样以先锋姿态出现的,还有对先进的自动化机器、飞机、照相机、电影播放机的崇拜。技术崇拜者深信技术可以改变社会,甚至可以自动祛除社会隐患。 (来源:新华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