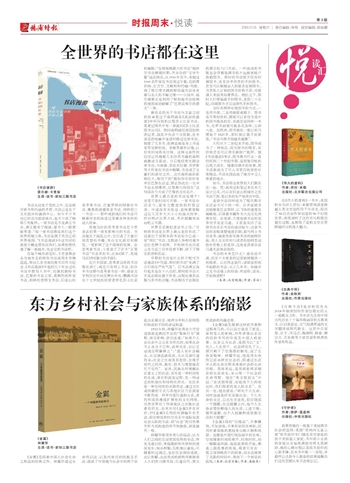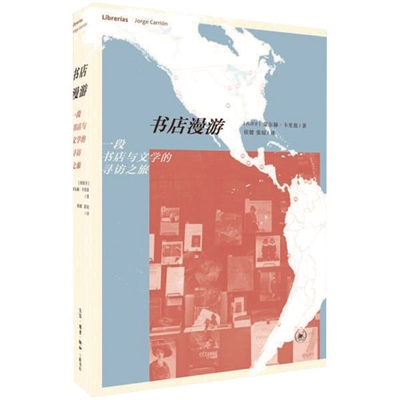在每个城市游览时,卡里翁都会去当地有名的特色书店或周末书摊逛逛,带回几本当地经典书目作为纪念。《书店漫游》中他将几十年去过的书店尽数写入书中,伦敦的敦特书店、巴黎的书友之家、莫斯科的作家书店、柏林的查特文书店、旧金山的青苹果书店、巴塞罗那的阿泰尔书店、雅典的波德里亚书店、剑桥的三一书店……那些或新或旧的书店目睹着历史的推进记录着各种各样的动人故事。
危地马拉的思考者书店是卡里翁去的第一家有影响力的书店。书店诞生于战乱之中,它引进了大量引领思想的书籍,举办文化派对和展览,一度影响了这个国家的发展。在思考者书店,卡里翁买了许多“正常书店”不会卖的书,比如《够了,危地马拉》和《暴力的手段》。
在许多国家,思考者这样的书店都在消亡,或是只有网上书店,但许多书店都与思考者书店一样,曾在文学和历史中站在舞台中央:鹦鹉书店在十七世纪的经营者曾是莎士比亚的编辑;“全球规模最大的书店”福伊尔书店辉煌时期,其举办的“文学午餐”远近闻名,从1930年至今,有超过1000名作家在书店用过午餐,包括萧伯纳、丘吉尔、艾略特和约翰·列侬。南丁格尔常光顾的斯坦福书店也有着与名人的不解之缘——小说中,福尔摩斯正是利用了斯坦福书店绘制的地图成功破解了“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一案。
最有名的关于书店与文豪之间的故事莫过于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中所写到的巴黎莎士比亚书店。笔者记得其中有一章就叫《莎士比亚图书公司》。那时海明威任美国驻欧洲记者,战乱中生活十分困窘,还未成名的他囊中羞涩时路过这家书店,他借了几本书,但窘迫地是身上并没有带足够的钱。老板笑着告诉他,以后有时间再来付钱。这种无条件的信任让怀揣着几本珍贵书籍的海明威激动又感动。日后他经常光顾这家书店,与庞德、菲兹杰拉德、乔伊斯等大作家在书店中畅聊,书店成了文豪们的派对之所。这对海明威的影响巨大,他写下的“假如你年轻时有幸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巴黎都与你同在”这句话在今天成了巴黎的文化名片。
世界上最古老的书店是哪个?光看开张时间可不够。一家书店存活至今,要有完整连续的经营记录。中途没有关张过,意味着要躲过近几百年大大小小的战火纷争、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多次国籍变动而屹立不倒。
世界吉尼斯纪录证书上写:“贝特朗书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书店。”这座位于里斯本的书店如今已成一家“网红”书店,无数游人争相对着书店红色牌子拍照。贝特朗书店自成立至今近三百年经营不断,留下了翔实的资料佐证。
早期的书店是什么样子呢?《书店漫游》中写道,那时的书店“充满了古旧和庄严的气息”。旧书店真正流行起来是在十八世纪,那时的书店大多是出版社旗下所有,出版社兼具出版与卖书的功能,书店相当于出版社的展示柜与门市部。一些流动的书贩也会背着装满书的大包挨家挨户推销图书。那时的书店里不仅有印刷图书,还有许多珍贵的手抄图书,甚至可以根据客人的要求定制图书,当然私人订制的图书价格不菲,对普通人来说类似奢侈品。相比之下,那时人们更偏爱手抄图书,直到二十世纪,印刷图书才完全取代手抄图书。
当时有两种存放图书的方式,一是用书架,二是用抽屉或箱子。图书是不带封皮的,顾客可以亲自为选中的图书挑选封皮,也就是说同样一本书,光看书封面可能各式各样、五颜六色。在欧洲,图书被统一装订的习惯始于1823年,那时装订器开始普及,“书店与图书馆越来越像”。
大约从十二世纪末开始,图书成为了一种商品,因为图书的稀有,其价值甚至可以用来做财产抵押。据《书店漫游》考证,图书典当行业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中期,直到复印机的出现才消失。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图书逐渐成为了可入寻常百姓家的日常物品,书店也因此成了城市中受人喜爱的地点。
如今,书店将全世界的人们联系在一起。梵·高用过的笔记本在米兰设计出来,可以在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买到,笔记本的生产地来自中国。
连锁书店同样成为了现代都市生活必不可少的一环。许多连锁书店就像星巴克那样,以飞快的速度攻城略地,引领着书籍作为大众文化消费市场。在美国,大型连锁书店的竞争对手是亚马逊。卡里翁采访了连锁书店水石书店的成功秘方,这家书店的老板清楚地意识到,要与网上书店竞争,就要发挥实体书店的独特价值,用人文关怀和与读者的独特互动弥补价格上的差异,这些是读者在亚马逊无法体会到的。
书店的未来是什么?谁也说不清,但至少卡里翁的记录能够提供一些线索。以后你去旅行,请留意那些不起眼的书店,买上几本书。如城市之光书店墙上的标语:欢迎你,请坐,开始阅读吧!
(来源:北京晚报|作者: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