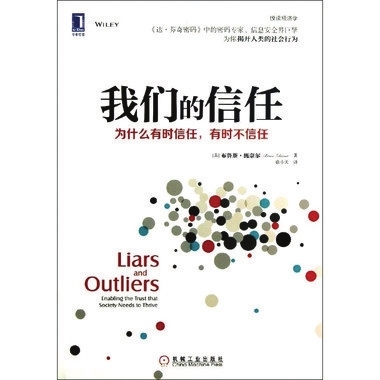尽管最糟糕的局面尚未出现,但当今社会和经济领域的确出现了信任危机,从微观层面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组织(企业、政府办事机构)之间戒备心的加重,到公司治理、金融、制造业外包等诸多领域的怪象频现,信任、信心都成了轻信无知的代名词。譬如,上市公司通过财务欺诈抬高股价,其高管团队从中获得巨额红利,却损害了信任这些企业的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互联网企业、地产企业、银行、保险公司、医院都声称最为严密安全的保护公民隐私,但批量贩卖隐私信息以牟利的做法却很普遍;品牌制造商通过公关手法,试图屏蔽产品质量问题和外包环节有悖于环境保护、儿童保护、劳工保护的细节,肆意愚弄公众;监管部门声称履行了交通安全监管的职责,但事实上许多公共交通工具却不是那么安全,以一定的几率上演安全事故。
世界信息安全界巨擘、顶尖的密码专家布鲁斯·施奈尔在其所著的《我们的信任:为什么有时信任,有时不信任》一书分析指出,社会压力是产生并维持信任的重要手段,也是迄今种种信任危机背景下,多数人选择诚信的根本原因:
其一,道德压力。绝大多数人不会盗窃,也不会乘人之危,这并不是周边存在威慑,而是源于道德自律,我们认为盗窃或乘人之危是错误的行为,愿意遵纪守法。
其二,名誉压力。这是一种来自他人对我们自身行为反应的压力,有时会变得十分强大。
其三,制度压力,通过对违规者施加惩罚及对顺从者特别是模范执行者表彰嘉奖来促使社会、群体成员遵循。
其四,防护机制。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为了促成合作、防止背叛、建立信任、强制服从都需要技能型必要的防护机制设计。
信任危机的出现,与上述四种社会压力的失效相关。道德压力的失效,常常源于社会成员身份的多样性。具体来说,我们既可能是某一个公司的雇员,又是消费者,还兼有公民身份,通过网络或媒体对公共议题发表言论。这几种身份在某些情况下会形成规则冲撞、利益冲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公司雇员在本企业出现有质量隐患的产品、涉及虚假宣传等问题时,放弃基本的道德立场。而名誉压力失效,与当今社会和经济体系变得大有关系,也就是说,如今失去名誉已经不意味着无法挽回的损失,与因背叛而获得的收益相比可能显得微不足道,很多人在因背叛脱离原先的社区、工作环境后,又成功建立起了一套新的名誉体系。
制度压力会带来对制度的迷信,许多人赞同通过法律制度来界定尽可能多的社会事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而今政府立法介入的领域,远远要比几十年前、一百年前及更早要多得多。制度越来越多,社会信任水平却越来越差,不能不说两者之间存在必然联系。首先,面面俱到的制度并不意味着对所涉及的领域都能形成有效管控,制度落实需要成本,制度过多、过繁导致无法落实,继而因大量个案葬送人们对制度的信任。其次,制度有其僵化性,形成的激励性可能存在偏差,甚至诱发不当行为。第三,过多制度可能导致制度“打架”,让人无所适从。
前三种社会压力的失效,正在催生出越来越发达的防护产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花费在风险内控和外聘审计上的钱越来越多,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手机杀毒产业变得红火,富人和公共机构的安防成本也不断攀升。
如前述,经济全球化需要建立全球化范围内的信任体系,但范围更广、更为复杂的社会和经济联系,以及技术革新让旧有的产生和维护信任的社会压力机制趋于失效。布鲁斯·施奈尔认为,这种情况下,不妨转换视角,将技术革新用于实施新的防护技术、推进新的范围更广的协调与协商。
《我们的信任》一书的结语部分给出了重新建立社会压力的诸多原则:推动互联网时代线上线下的社区交流,重新增加道德压力、名誉压力;使用防护机制调整道德以及名誉压力;协调相关科技的制度压力;让违反制度和破坏防护机制的行为者,受到足够严厉的惩罚;推进公共参与,避免权力集中在个别部门或官员手中;实现政府机构和企业运作的透明化。 (来源:新华读书)